
董事长随笔
Chairman's Essay
八面书香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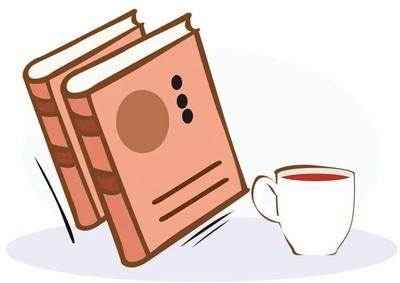
我1979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,文科五门考试总分数223分,数学只得了5分,连最简单的一道满分8分、证明勾股定理的题也没有完全答对。结果,只好去读了中专,据说是物资学校79级入学分数最低的一名应届高中生。
我把这份高考成绩通知书,装进相框挂在了办公室的墙上,当作警醒并有怀念青春之意。有人不让我挂这个,说多没面子,对年轻人也没有好影响,要挂就挂立功、获奖之物。我没理会,不觉得这个寒碜,也绝对不是要和励志较劲,只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真实经历而已。
当年没考上大学,不仅是因为贪玩,还时不时就与同学武力相向,就在高考最后一门交卷之后,我还和几个哥们儿在五十四中考场外的铁道边约架呢,所以,我考不上大学也是必然结果。
其实,我是知道要好好学习的,也知道读书越多越好,最起码能上大学,分配到好工作,更有机会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。
爸爸对我说过,多读书、读好书能使自己聪明,能辨别是非,能更好地做人。爸爸是补习后的高中文化,喜欢读书,书柜里整齐地摆放着他看过的“马恩列斯毛”的经典著作,全是精装本。爸爸也买过很多哲学、文学和关于艺术的书籍。他读书有个习惯,就是在自己觉得重要的语句下面,用蘸水笔画上红道道儿。妈妈平时将书柜收拾得很整齐,几乎一尘不染。所以,我自小就觉得书籍是一种很值得敬重、很严肃、很庄严、很神秘的存在。
我真正觉得书籍与个人命运相联系,并应视为珍贵物品,是源于那个特殊时期,妈妈保护书、爱护书的一件往事:她用新床单包裹抄家者要拿走的书,那场面叫我刻骨铭心,永远难忘。
1967年春天,我们家还住在河东区棉五二宿舍一座日式联排小楼的二楼。一天上午,只有我和妈妈在家,楼下开来一辆四轮小货车,车上下来五六个人,直奔我家楼上,木板楼梯被踩得咚咚作响。他们跟妈妈简单、生硬地讲了几句话,便直接打开房门、储物间的拉门及室内书柜的门,将里面“马恩列斯毛”的书、古籍和中外文学书籍全拿了出来,半扔半放地散丢在地板上。而后,他们挨着本儿地翻看,好像要找什么东西似的。
这些人不吵不闹,快速地翻看着,看了不一会儿,终于不这么看了,其中一个人站起身来不容置喙地对妈妈说,这些书要全部拿回去仔细检查。
妈妈原本是默默地站在一旁,看到他们没像其他抄家的人那样胡来,还主动地给他们倒了白开水,但当听来人说要把这些书全部带走时,她神态有些变了,看到地板上有的书散页了,有的掉皮了,有的弄脏了,她开始心疼那些书了。妈妈镇定了一下,伸手阻拦说,你们等一等,我去拿个布单子。她迅速地从一个立柜里,拿出来一块儿全新的、叠放整齐的粉红色杭州提花被面,那是给我已经随上山下乡运动回乡务农的大哥准备的。妈妈将被面铺展在地板上,把散乱的书一本本地整理好,整齐地码放在被面上,有个三四十本后,就将被单对角系成了个包袱。而后,她又拿出一块干净的花布床单,如法炮制。妈妈边系着包裹,边说:“你们小心一点,这些书以后还得看呢。”也许是听多了别人抄家的事,所以当时妈妈并没有过多紧张。这些人走后,不到六岁的我躲在妈妈身后,还是感觉到了她的惊慌和错愕。
爸爸当时在一家棉纺厂当厂长,是出生入死的“地下党”,那时被列为当权派和走资派。晚上,爸爸回来了,妈妈跟他说,我忘记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了。还有,咱们的床单什么时候能还回来啊?爸爸心疼地说,就算白搭进去个好床单吧。别想了,人比书重要。可妈妈说,你不是拿书当宝贝吗?我那时还小,听不懂这些话,但我觉得妈妈保护书的行为,其实是对爸爸爱书的一种支持。
因为这次抄家,书籍给了我万千的向往和迷恋,我宁愿冒险翻看那些留下来的书籍。后来,还有两件跟这次抄家相关联的事,一是爸爸跟妈妈说,是因为有人知道他看书,爱在句子下面用红笔画重点,被反特电影看多了的厂技校学生盯上了,有学生举报,这可能是潜伏特务的密码或暗号,所以才被抄家的;二是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,当过警察、那时已经调到棉纺厂的三哥,他到同事家聊天时,见到了一本精装的《莱蒙托夫文集》,扉页上有爸爸的一方篆字名章,三哥一眼认出了爸爸的名章后,又看到书中有爸爸用蘸水笔画的红道道儿,就问这书是从哪来的?那同事回答,是他哥哥不知道从谁家“顺”回来的,以前有好几十本呢,翻翻就都点炉子烧了,只剩下这些硬壳的了。
三哥回家告诉了爸爸,爸爸平时不爱多讲话,听到这事也没有急躁,只是像平常一样叹口气,说了句“也看书就好”就过去了。三哥听了爸爸的话,也没再去找事儿,跟那个同事说破。
这些由书引出的良知和勇气、侠义和真情,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,促使我开始自觉地读书、学习。尤其是我参加工作后,有机会考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,更是下了一股子狠劲,我想用“破坏书的方式”达到读更多书的目的,将被懒惰偷走的时间重新夺回来。
1981年,我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区政府工作,算干部。当时社会上急需各种人才,政府广开学路,创立了可供业余时间学习的广播电视大学和职工大学,毕业后国家承认与全日制大学一样的同等学力。1982年,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首次在全国正式招生,学制三年,如果考上,每周有两个半天的集中学习和几个晚上的自听电台广播学习,报考条件是必须经得单位同意。刚上班的小青年拿着工资利用上班时间上学,一般单位根本没门儿,区政府人事室原则上不鼓励,因为当时我工作的部门,一共才十五六个人,有五六个人要报考,如果都考上了,真的是会影响工作了。
我们的主任叫裴玉川,当时已经快六十岁了,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革命,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做过大厂领导,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过。区政府那时在地震震塌了的原址上搭建的临建里办公,有六七间办公室,同事们中午没有午睡的习惯,多数人下棋、看书、聊天,这是跟领导沟通事情的好时机。
裴主任听说我们同届分配来的几个人要去考电大、职大,当时没有表态,但有的科长表示反对:怎么好事都叫你们赶上了,要是都考上了谁工作?说的也是实际情况。但我想努力一下,先去找了师傅张新乐、组长杨静珍,保证一旦考上了绝不耽误工作。他们考虑再三,终于同意了。
还没等我去找科长,裴主任就召集大家开会了,他对我们要考学的人说:“你们能到区政府工作很不容易,现在又有了上学的机会,若考上了不仅能学到知识,以后提拔干部,学历还会起到作用。所以,给你们机会,我同意你们报考,人事那里我去讲。但是有一条,考上学后绝不能耽误本职工作,本分做人、努力做事,才有可能有前途,这对国家也是好事。”事后得知,机关里就裴主任最为青年干部争取机会。我们很幸运,遇到了一位胸襟开阔、能充分考虑年轻人命运和国家利益的领导。因为这,裴玉川这名字我一辈子不会忘。
报考之后,我就下决心一定要考上。我们单位六个人报考电大,最终只有两个人考上了,我算一个。我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,更没有博闻强记的读书技巧,我用了可能是最笨的办法去做最后的冲刺:在离考试还有最后两周时,我将复习参考书看过一页撕一页,看完一门就毁一本,自己给自己结课,这也是自绝后路。我的学习方法是“强刺激”,逼自己“记住”,这不是一个好方法,但对我自己管用。我如愿考上了电大,这是我的运气。有人说运气是一个人软实力的一部分,这话我信。我偶有不正、不智之时,便有运气相伴,我的运气都来自亲人、同事和朋友,一颗颗向善之心护佑着我,我愿意离他们近一些,接受他们美与善的传递与浸润,他们推着我朝前努力,融合和铸造了我对于学习的坚持与耐心,克服困难的沉着与勇敢,对理想的向往和对亲朋的情义,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与忠诚。
现在,读书成了我的一种习惯,不仅仅是对父辈的一种精神继承,还可以使生命活得更加扎实和宽广,可以比别人看到更多的美好和快乐。我喜欢书,尤其要将其干净、整齐地放在书柜中、书桌上,就是散放也要尽量规整,那样看着舒服。如果是在陌生人处看见人家码放整齐的书,我立马会生出几分敬意和尊重。当然,如果看见那种专为办公室或客厅书柜置放的只印有书名、起装饰作用的纸板儿,我也会很反感。
书是有灵性的,不仅要当作学习、消遣、欣赏之物,而且还要善待它,并将它作为一种情感的表达,要保护好书。无论纸质书、电子书,或者以其他形式存在的书籍,多读都会充实自己,即便常常面对困难也不会自己想不通。读书不是万能的,不读书、少读书是万万不能的。只要多实践、多读书,就会信心怡然、一切自然,积善、致仁、成德,就会尽觉满眼阳光、八面书香!
(作者 王育英 题图 张宇尘)

(本文刊登于《天津日报》2025年3月14日 12版)
